
小时候,也就是50多年前,全家客居在山东平阴山区的一个小村栾湾。当时父亲是邮电所的所长。邮电所设在山村最高处的一个山坡上。院子里有一些空地。已是50多岁的父亲利用工余时间,把地开起来,捡出土里的石块,除了种上南瓜(当地叫北瓜)、洋姜,还在地边上种了不少向日葵,当地人叫葵花。
1958年我7岁。
每到春季,父亲先用铁锨挖好一个个土坑,在坑里上上一些牛粪驴粪人粪,浇上水,等水渗下去后,把几粒饱满的向日葵种子撒在里边,盖上土,再用锨轻轻地拍一拍。大约六七天之后,土坑中就钻出几棵幼嫩的黄绿的苗芽来了。如再下上一场春雨,苗芽很快就长高了,长出了几片叶子。待苗芽长到一扎多高时,把长得矮的拔掉,只留一棵长得最旺的,让它独自生长。如一窝苗中有二三棵长得茁壮的,父亲就移出一两棵来,栽到别处,坑中只留一棵。
渐渐地,向日葵越长越高,叶子越长越大。秆儿越长越挺拔,越粗壮,待长得比大人还高时,就到了盛夏,梢头上就长出翠绿的花盘来了。花盘微微低着头,也是越长越大,最大的有大瓷盘那么大了。盘中金黄色的花瓣也随之盛开。花盘早上是冲东方的,当火红的太阳从东山上升起来时,花盘就随着太阳的移动由东向南,再由南向西缓缓地转动。就像一队队士兵,向一位检阅的将军行注目礼。
在向日葵生长期间,父亲仍经常给它们浇水、追肥。父亲说,只有水和肥料足了,它的叶茎才长得更加旺盛,种子才长得饱满。只是,有时刮大风下大雨,向日葵被吹歪了,吹倒了,父亲就用树枝或上一年的向日葵秆子把倒了的支起来,用草绳捆住,再在根部培上一些土。
父亲下了班,常去看他的那一排排向日葵,就像看他的心爱的孩子。
向日葵快成熟时,常有馋嘴的麻雀、花喜鹊、山雀落到花盘上啄那香甜的花籽。我发现了就去轰它们。不过损失不大。秋季,也是蚂蚱、昆虫长得最胖最肥的时候,鸟儿们的主食还是那些会飞会跳的活食儿。
父亲种向日葵和照料它们时,我也在一旁帮忙。到了我十一二岁时,就可以独立地干这些活了。
向日葵的叶子挺大,大的像一把扇子。为了让主要的水分养分供花盘生长,要把下边的叶子打一些去。打叶子时,要从叶柄的中间打,以免往下劈时把秆皮儿劈下来。那叶子有一个用处,就是喂羊。别看那叶子挺粗拉的,上边还有些小刺,但山羊却不怕,而且吃得挺香,挺带劲儿。我家曾先后养过三只山羊,有一只母羊还生了一只可爱的小羊羔。
到了收获的时候,父亲就去先摘成熟最早的花盘。当然最先品尝的是我。花籽又嫩又甜又香。我也去摘向日葵的花盘。我个子矮,够不着,就踩个凳子,或干脆把向日葵扳倒。父亲还让我给公社(现在叫乡镇)的干部叔叔和邻居送去花盘,让他们也分享这劳动的果实。
也有的花盘在夜间被人偷去了,而且专门偷最大的。对此,我很心疼,很生气。父亲却笑着说,摘就摘吧!反正向日葵种了就是给人吃的,谁吃都一样。再说,这山这地还是人家的呢。
父亲种的向日葵品种有好几种,有长的、扁的。还有一种紫黑色的,刚摘下来吃的工夫,吃得嘴唇、牙齿、舌头都是紫黑色的,手指也是紫黑色的,后来父亲就不种这一种了。
每年,父亲都留出一两个籽粒最饱满的花盘,做为明年的种子。剩下的花盘,用绳子拴起来,挂在墙上。花盘渐渐干了,可以把花籽搓下来,保存好,到冬天或过年时吃。母亲把花籽用锅炒熟,吃起来更香。那当年收的葵花籽,比如今超市里卖的这些什么盐渍的、五香的香多了。
如此一年一年,我家在那个小山村住了6年,父亲在那个山坡上种了6年向日葵,我也从7岁长到了13岁,从一年级上到了初中二年级。而且,学习成绩一直很好。就像《小白杨》那支歌中唱的:“它长我也长。”
小时候,也不知葵花籽有多种的营养成分,还有别的用处,更不知葵花籽还可以榨油,可以放在糕点上,可以做五仁月饼,还可以做菜。
想来,向日葵最大的特色就是向往阳光,向往光明,迎着阳光开放。它在干旱、贫瘠的山地里也能顽强地生长。它对土地的要求甚少,而长出来的,却是碧绿的叶子,开出来的是金灿灿的花朵,结出来的是饱满的种子。
向日葵给世界带来了香甜,带来了财富,也带来了美。
1964年8月,父亲因病在平阴去世,我和母亲、姐姐离开了栾湾那个小山村,就没再种过向日葵,也没再吃过那么香甜的葵花籽。但我小时候跟父亲学会了种向日葵,如果以后有一块空地,我还会种它的。
2012年9月18日10时16分于济南长耳居
(九一八81周年纪念日)
(恰逢中国人民群情激愤,反对日本侵占我神圣领土钓鱼岛)
2013年6月16日修改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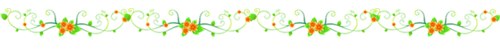
有令峻 执笔
1951年3月生,山东省作家协会创作室原副主任、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长篇小说当代都市三部曲《夜风》、《夜雨》、《夜雾》等专著26部,计800万字。获奖100多次。
